新闻中心 
山西高院发布2024年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民主与法制网讯(记者邵春雷 □刘敏)近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 2024 年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涵盖著作权、商标、专利、企业名称、技术合同、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类型,涉及传统文化传承、销售模式创新、专利技术应用、知名商标和商业秘密保护等领域。此举既展现知识产权严保护的基本立场,又防范权利人权利滥用,兼顾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突出反映了山西法院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更好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的工作成效,对于提升全省知识产权审判质效,提高公众尊重保护知识产权意识具有很强的示范、引领意义。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案例不仅是司法裁判的具象呈现,更勾勒出山西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实践路径从传统文化传承到数字经济新业态,从民事纠纷化解到刑事犯罪打击,司法正以“解剖麻雀”的方式,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在“王某诉某旅游文化公司著作权侵权案”中,原告父亲创作的百家姓图腾作品被景区擅自使用,索赔 300余万元。法院认定侵权成立的同时,注意到作品承载的姓氏文化属性与景区的公益传播目的,最终以调解结案,景区支付 40 万元授权许可费。这一案例打破 “一刀切” 的侵权处理模式,凸显著作权法 “鼓励创作与传播”的双重价值。
“当作品取材于公有领域,且具有文化传播属性时,司法需要在权利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间找到平衡点。”山西高院民三庭法官指出,本案若判决销毁价值数百万元的侵权甬道,将造成社会资源浪费,违背民法典绿色原则。调解结案既保障了著作权人权益,又让传统文化载体得以保留,实现“保护+传承”的双赢。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某商贸公司批量诉讼牟利案”。原告针对电商平台提起 794 件诉讼,涉案摄影作品独创性低且未采取保护措施,法院最终将1万元索赔压减至600元。这一判决剑指“维权产业化”现象,明确“诉讼不得异化为牟利工具”的司法导向,警示权利人需合理行使权利,避免过度商业化对市场秩序的损害。
商标领域的典型案例集中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适用。“马某明诉某公司晋得利眼镜店案”中,被告自1987年使用“晋得利”标识,早于原告2005 年的商标注册时间,且在当地形成较高知名度。法院认定被告享有在先使用权,驳回原告全部诉求,明确“商标注册权不得对抗善意在先使用”的规则。
这一判决打破“商标注册即拥有绝对权”的误区。法官解释,商标法不仅保护注册权,更禁止“抢注他人在先使用且有一定影响的标识”。此案中,被告持续使用近20年,已形成稳定的市场关系,若强制更名将损害消费者信赖,违背 “保护在先权益”的立法初衷。
在刑事领域,“冯某宏销售假冒名牌服饰案”与“张某销售名牌白酒空酒瓶案”则彰显对商标权的立体化保护。前者销售金额超105万元,主犯获刑四年并处罚金21.5万元;后者通过回收空酒瓶整理销售,被认定为“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体现司法对“源头治假”的重视。“即使未直接生产假货,为制假提供关键材料同样构成犯罪。”检察官指出,此类判决旨在斩断侵权产业链,从上游遏制制假售假行为。
专利案件中,“等同侵权”与“新型销售模式责任”成为焦点。“李某文诉梁某媛实用新型专利案”中,被告以“磁力拉绳材质不同”抗辩,法院认定木球与磁铁球功能、原理实质相同,构成等同侵权。这一判决明确,“以基本相同手段实现相同功能”的技术特征替换,即使是材质、外观的非实质性变化,仍属侵权,为“微创新 抄袭敲响警钟。
在电商领域,“杨某一件代发侵权案”具有典型意义。某塑业公司享有名为“冰盘”的外观设计专利。后发现杨某在其经营网店所销售的塑料盘侵犯了该专利。故诉请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和维权合理费用5万元。
杨某辩称,其采用“一件代发”的经营模式,即消费者在购物网站上下单后,由第三方供应商直接发货给消费者,并未直接经手货物,不构成销售行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而法院认定其经营行为本质上属于商业销售,需承担审查义务。
随着“一件代发”“无货源电商”模式普及,此案明确:经营者不能以“非传统销售”为由规避责任,平台卖家需对商品合法性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否则将面临赔偿风险。
这些判决传递出清晰信号:专利保护既鼓励真正的技术创新,也打击“换汤不换药”的模仿行为;新型商业模式并非侵权“避风港”,合规审查是从业者的必要功课。
在企业名称权纠纷中,“谱恒科技公司案”厘清了字号重复的侵权认定标准。原告谱恒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拓展山西市场,在山西注册含有“谱恒”字号的企业名称时,发现该字号已被山西谱恒科技有限公司注册使用,认为其侵犯了自己的企业名称(商号)权和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故诉请判令被告变更企业名称并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
但法院指出,被告登记时间合法、经营范围不同,且未造成公众混淆,不构成侵权。最终通过调解,被告主动更名以避免市场误认,既维护了企业名称注册制度,又体现“谦抑司法”的智慧。
技术合同纠纷中的“某汽车制造公司案”则聚焦验收标准模糊问题。某汽车制造公司与某技术公司签订《皮卡项目设计开发合同》,约定根据某汽车制造公司的需要,基于成熟产品底盘平台开发皮卡车型。合同约定交付的技术成果为车身数据,验收标准以某汽车制造公司的设计标准为准,需要技术成果具备排他性、独创性、可拓展性、通用性、实用性及经济性等。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合同约定的“排他性、独创性”等抽象指标无法作为验收依据,法院依据行业惯常标准认定交付成果合格,判令支付合同费用。
此案警示市场主体:技术开发合同需明确具体验收条款,避免因标准模糊引发纠纷,凸显司法对技术成果转化的积极推动作用。
“孙某兵等七人侵犯商业秘密案”堪称近年来山西商业秘密保护的标志性案件。2020年12月,被告人孙某兵等七人共谋利用在某公司任职期间各自掌星空体育登录入口 星空体育在线官网握或非法获取的商业秘密成立新公司,生产与某公司同样的产品进行销售获利。2020年12月30日,新公司成立。七被告人为隐瞒身份,由他人代持股份,利用已获取的原公司商业秘密促使新公司快速投产,并通过原公司的销售渠道抢占市场。2021年2月至2022年7月,新公司销售获利300余万元。检察机关因此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最终七人均获刑三年并处罚金。法院强调,商业秘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即使员工离职,非法获取、使用原公司技术信息仍需承担刑事责任,且附加“从业禁止”以防止二次侵权。
此案反映出山西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司法护航。数据显示,2024年山西法院受理商业秘密案件同比增长 45%,且多集中于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对于跳槽侵权窃取技术等行为,司法保持高压态势,就是要让创新者流汗不流泪。”
法官表示,判决设置从业禁止,既是对侵权者的惩戒,也为行业划定了“保密红线”。
十大案例犹如十面镜子,映照出山西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多维图景:既坚决打击恶意侵权、批量诉讼等乱象,又审慎平衡公益与私权;既守护传统领域的创新成果,又回应数字经济、电商新模式的治理需求;既通过民事赔偿遏制侵权行为,更以刑事处罚斩断犯罪链条。
这些案例的价值远不止于个案裁判。它们通过明确“等同侵权”“在先使用”“商业模式审查义务” 等法律适用标准,为市场主体划定行为边界;通过调解、判决等不同处理方式,展现司法在多元利益中的平衡智慧;通过“典型意义”的阐释,向社会传递“尊重知识、鼓励创新”的价值导向。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的背景下,山西高院的实践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不是简单的“维权”与“打击”,而是需要构建“保护-激励-平衡-发展”的生态系统。当司法裁判既能为权利人撑起“保护伞”,又能为社会公共利益留足空间;既能惩戒违法者,又能指引合规经营,才能真正实现“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终极目标。
随着这些典型案例的传播与适用,更多市场主体将从中汲取经验、收获教训,在法治轨道上开展时代创新活动,共同书写山西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这或许正是“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的深层意义让司法的阳光,照亮每一个创新的角落,让每一个创新者能更加从容坚定更加意气风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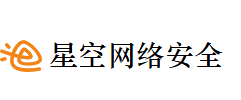
 2025-05-01
2025-05-01 浏览次数:
次
浏览次数:
次 返回列表
返回列表